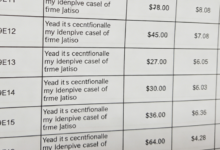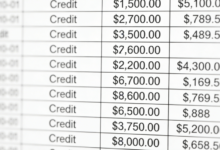最近文化圈一件很热闹的事情就是作家冯唐翻译的泰戈尔名著《飞鸟集》由于被批低俗而遭遇出版社紧急下架,出版社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我们接收到读者和媒体对于书籍的负面反馈。我们决定召回书籍,对译文中的内容作出重新审议后再作出后续决定。”
事件伊始,冯唐很淡定,他在采访中说道,“我相信历史和文学史会给出判断,让时间说话,文学史说话。”可没过两天冯唐坐不住了,在微博上晒出自己当年考托福的满分成绩单。这一举动非但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反而令他遭到了更多的批评。南方人物周刊发文称:”不管冯唐如何为自己辩解,晒成绩单的举动或许是被出版社逼迫炒作,或许是被不可说的力量左右而无处发泄,但仅就这一本书而言,冯唐的翻译水平是完全不被认可的。不光业界痛心疾首,民间读者也被吓得不轻。……他的译本追求押韵过了头,有小部分像是文青金句,更多的像是强行扭动的二人转,有着下流的小聪明。”但支持冯唐的专家和网友似乎也不在少数,印度文学研究专家郁龙余就说,”冯唐的译作更符合原作格言诗的面貌”。
眼下文学翻译还是很热闹的,主要集中在名著和当代作品的翻译上。名著多半是重译,因为销量大,各地出版社都踊跃组织翻译。就像此次翻译的《飞鸟集》虽已有郑振铎老先生的珠玉在前,但冯唐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实说白了,背后就是市场的需求和利益的驱动。去年底,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自媒体频道也开出了500元/千字”史上最高翻译费“重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此,有人质疑,用这种众筹的方式来翻译和出版经典的做法是否有些草率、不够严谨,是否能够保证翻译的质量。
一直以来经典著作的翻译对于译者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这种诱惑或许不单单是来自于金钱,另一方面也是译者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毕竟翻译名著远比翻译一部不为人知的作品来得有挑战性。这大概也是《莎士比亚全集》、《堂·吉诃德》、《老人与海》等许多经典名著的中译本层出不穷的原因吧。所以,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经典重译现象?小九君任性搜罗了几家的看法,以馔读者。(节选)
赵武平(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一本名著能够出版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以说一定是一个人类知识集大成的智慧传承的典范作品。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当成一个故事,它进入中国总是要找一个最合适讲故事的人,大家才愿意听,或者说听故事的人才能更大限度地还原和感知故事本身。翻译和写作在不侵犯知识产权和版权的情况下,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行为。因为读者也有层级之分,普通的、成熟的、专业的甚至学术的,他们在不断地成长,也在不断地筛选、比较,讨论译本的好坏,是否超过原有译本的学术水准等,这都不是太难的事。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这涉及到一个翻译水平的问题了。超过名译是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多翻译家倾其一生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那么高的水平,更何况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要挑选这样一个译者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到底,如果你的水平能够超过前人,当然欢迎,否则粗制滥造的翻译就没有必要了。
陈及(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很多著名的译本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大家会有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新译本也依然不能保证文本就能让所有人满意。一方面是翻译能力的问题,不论是翻译效果的信达雅,还是翻译者本身的功底、学术态度,等等,都是如此。如果是一些年代较为久远的经典译作,对其做局部的调整,我认为是可以的,但要所有东西推倒重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或许产生的问题会更多。
郭宏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荣誉学部委员):不为名往,不为利来,在翻译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平常心,这是搞好翻译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翻译不可能没有一个目的,或者为了研究,或者为了欣赏,或者为了炫耀,或者为了稻粱谋,这些目的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种种的目的占了上风,成为获取名利的功利手段。
郑克鲁(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著多半是重译,因为销得动,各地出版社都踊跃组织翻译。有译得好的,也有错误百出的,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古典作品中还有不少值得介绍的,这对文化积累来说非常重要。
“信、达、雅”是文学翻译广受认可的标准,文学翻译追求的效果究竟是忠实原文还是在原文基本上结合本国语言的再创造,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就此次冯唐的译作来说,小九君觉得其中也不乏一些精美的译句,对照原文,这些翻译似乎也确实更能体现诗歌的意境和所要表达的深意。翻译界一直流行关于“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似”、“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间的争论。小九君的看法是,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形似还是神似,既然是流芳百世的名著,其中的文字肯定都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因此最大程度上保持原文字的韵味,这或许才是好的翻译吧。
 九九译
九九译